作者:杨祚合
大年初二开始,城里乡下各式各样的轿车摩托车电动车,涌满了街道,走亲串友的队伍川流不息。人们带着包装精美的饮料食品,欢声笑语,进进出出,热闹非凡。望着满街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群,不禁又回想起几十年前过年背着包袱走亲戚的情景。
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,乡村几乎没有车辆代步,走亲串友全是步行。大年初二就开始走亲戚了,一直到正月十五之前,乡间大路小道上全是背着包袱看亲戚的人们。有妇女领着孩子的,有少年儿童,有老人,更多的是壮年男人,在儿童的行列里常常有我的身影。
在我的记忆里,我常去的是姥姥家和姑奶奶家。包袱里背的是母亲准备的十斤白馍馍和二斤糕点,白面馍馍是家里为过年留的小麦从馍馍房换的,专门用来看亲戚和待客。白面馍馍要点上花,糕点大都是羊角蜜或三刀子之类,用包装纸包好并加一方红纸条用纸绳系上,显得十分喜庆。那时乡村人们以地瓜高粱为主食,平时很少吃上白馍馍,因此过年走亲戚白馍馍就成了时兴的礼品。来来往往看亲戚的,都要背上一包袱白馍馍,外加两包糕点或红白糖。走完一家留下一部分后,回来再添几斤配上,总要足够十斤。同样,糕点也要配够两包或四包,再去走另一家。这样来来回回,不停添配,直至走完所有的亲戚。最初的那些馍馍都裂开了花,干得咬不动了,家人才舍得吃。
那时我才十一二岁,最初去姥姥家都是哥哥带我去,从家到那里有十几里路,十几斤的包袱哥哥和我轮流着背。走一段路,就停下歇会,越走越慢,走到姥姥家就该吃晌午饭了。到了姥姥家,顾不上跑得两腿发酸,总要先给姥姥舅舅妗子拜年,姥姥早就准备了压岁钱,先是一元两元,过了几年增加到五元。接过压岁钱心中十分高兴,要知道那时一两元钱就很稀罕啦,父母给的压岁钱常常都是一毛两毛的。和表弟们玩一会儿,就开始吃饭,那时没有大鱼大肉,有时炒两个菜,有时就光吃饺子。姥姥家的饺子多少有点肉,比我们家的好吃,我和哥哥有时要吃两大碗。
后来几年,我渐渐大了,再去姥姥家就自己背着包袱去。十几斤的包袱虽不算重,但跑十几里路,每回都累得够呛。为了省点力气,母亲让我带个擀面杖,挑起包袱,这样半扛半背,走起路来就轻便多了。到了姥姥家吃过饭,有时还要等一会才能回家,因为舅舅要接我的包袱去看他的亲戚,他回来我才能走。有一回,舅舅的亲戚又接舅舅的包袱去看别的亲戚,舅舅回来时就比较晚了。姥姥要留我过夜,我说家里第二天还要用包袱的东西去走亲戚,说什么也不愿意,姥姥只好不再留我。我背起包袱急急忙忙往家赶,看着太阳越来越低,心中更是着急。于是走一段,跑一段,汗把棉袄都洇湿了,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了家,累得躺在床上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。
去姑奶奶家就好多了,离我家向东只有四五里路,很轻松就走到了。同样是十几斤的包袱,倒显得很轻巧,不知不觉就到了姑奶奶的家门。那时姑奶奶已七十多岁,满头银发,十分和蔼。由于我是家中弟兄几个里的老小,姑奶奶对我非常疼爱,专门留些好吃的给我。表叔在煤矿上工作,家里生活条件较好,到了他家我可多吃点好东西解解馋,多是些在家没吃过的。吃过饭,姑奶奶常领我去村东田野里玩。不远处就是大山,姑奶奶说那山上长满了松柏,大山深处还有什么神仙洞,很好玩。我想像着那高处的美丽和神秘,十分向往,盼望着长大后一定要身临其中。吃饱玩足回家时,姑奶奶总出门送我好远,并给我五元压岁钱,交待我放好,我也恋恋不舍地向姑奶奶告别。
背着包袱看亲戚持续了好多年,我也在一年年步行中长大,品尝了岁月的艰辛和童年的快乐。直至80年代,走亲戚告别了包袱和步行,家家有了自行车代步,白馍馍再也不是稀罕礼品,取而代之的是包装精美的大包小盒的糕点饮品。年后的路上,再也看不到那背着包袱走亲戚的别样风景了。如今摩托车轿车逐渐普及,出行更是方便极了,过年走亲戚,油门一踩,即可出发,只愁路上堵车了。
岁月匆匆,几十年转眼过去了。每逢过年走亲访友,当年背着包袱走亲戚的情景总会浮现在眼前,让我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。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,亲眼目睹了太平盛世、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。如今走亲戚,成了年后假日的一次次舒心旅游,亲友相聚,美酒佳肴,其乐融融,对比当年,真好似换了人间啊!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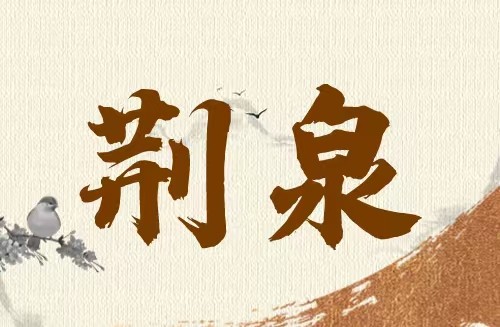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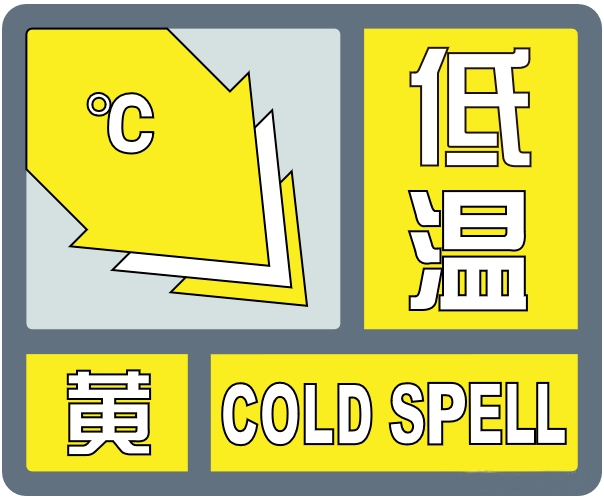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