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马润涛
咔嗒,咔嗒,咔嗒,织布梭子在梭槽里不紧不慢地来回跑着。姥爷坐在织布机上,两只脚踏着机板不停地上下踩动。他左手推着梭槽前后动着,右手不停地上下拉动着机绳。这动作配合极为协调,就像在演奏一支交响乐。一盏煤油灯挂在墙上,在昏黄的灯光里,姥爷的身影映在墙上,就像皮影戏里的一个人物剪影。
梦为心生。人老了总爱回忆以前的事情,特别是童年的事情。这是姥爷在世时早年织布的一个场景,不知在梦中重复了多少次,久而久之,那咔嗒咔嗒的机杼声,便时常萦绕在我的耳旁。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姥爷家有一台农村老式织布机,就摆在姥爷家的堂屋里。我每次到姥爷家,只要堂屋门敞开着,一搭眼就能看到那台织布机。
姥爷织布,多在农闲的时候和晚上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晚上织布,就像我上面描绘的场景。通常情况下,晚上喝完汤,姥爷从桌边站起身来,先是用手抹一下嘴唇,然后再用手捋一捋胡须,接着走到织布机前坐下来。可他这时并没有忙着织布,而是从织机旁拿过烟袋包和烟袋,装上烟叶,再掏出火石、火镰和火煤子。姥爷吸烟从来不用火柴,也可能那时候小山村里根本就没有火柴,都是用火镰打火。嚓嚓两声,姥爷打火一般不超过三下,火星飞溅到纸媒子上,接着“噗噗”吹两口,纸媒子瞬间就燃着了。他点着烟锅里的烟,先猛吸一口,稍作停顿,尔后吐出一个白色的烟圈。等一锅烟吸透了,他把烟袋锅往鞋底下猛磕两下,把烟袋往旁边一搁,这才从从容容地织起布来。饭后一袋烟,胜似活神仙。姥爷在世时,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生活习惯。
姥爷织布的时候,姥娘已经收拾完桌子上的碗筷。她这时会拿一个蒲墩过来坐下,把一旁的我揽到她怀里,哼着教我不知多少遍的歌谣。姥娘也有不哼歌谣的时候,在静谧的夜晚,姥娘用手轻轻地拍着我,静静地看姥爷织布,听姥爷演奏那支百听不厌、亘古不变的古老乐曲。每晚,咔嗒咔嗒的机杼声,几乎成了我的催眠曲,我常常在机杼声中慢慢睡去。因而,我从不知道姥爷晚上织到什么时候睡的觉。
春耕秋收,夏长冬藏。什么样的季节做什么事情。姥爷一个冬天都在织布,不过这时已不是在堂屋里,而是在地庵子里。姥爷家前面有一个大空园子,周围长满了树木,中间有一块空地,姥爷在上面种了几畦菜。等菜收割完了,已经到了暮秋。姥爷找自己的两个侄子,帮他挖掘搭建地庵子。先把坑槽挖好,再把织布机拆了抬来安装好,最后才把庵子上面搭建好。那时农村冬季取暖不像现在都安上了土暖,一般家庭有个火盆就算不错了,并且烤火烧的也多是秫壳子和谷糠。有条件的也有挖地庵子的,但极少,一个村子也没几家。挖掘搭建地庵子是北方人越冬的一个创造,那时在各个村庄都可以看到。地庵子的确是冬季取暖最好的去处,当外面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时候,这里却温暖如春。姥爷在地庵子里织布时,我和姥娘也在地庵子里面,姥娘一旁做着针线活儿,我就在一边玩石头子儿。
在我的印象中,在姥爷的村子里,人民公社前姥爷家过的日子是比较富足和殷实的。姥爷家不光地比一般人家多,姥爷还比别人多了一门手艺。我记得在姥爷家的一日三餐中,最常吃的饭食是绿豆面条,最常吃的菜是香椿芽、干虾炒鸡蛋。这两种饭菜,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后者,在我眼里它就是珍馐,也是我童年饮食中的独一美味。至于绿豆面条,也可能是经常喝的缘故吧,嫌它有一股豆腥味,后来多年都不喜欢喝它。因为我姥爷家的生活比我家好,我从四岁多就到了姥爷家,要不是后来我爹接我回去上学,我还会赖在姥爷家。有一句话说,外甥是姥娘门上的一条狗。许多年后,我头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曾自问:我也是那条狗吗?
我回到家后才知道,在姥爷织布的那些年里,我娘也没闲着。她每年都把自己家的棉花弹了纺成线,然后再把线穗子用籰子络了,然后用浆子把络好的线浆洗了。那些年我们家穿的铺的盖的棉布,差不多都是我姥爷织的。
姥爷织的布叫山花布,就是用山地里种的棉花织成的布。后来时兴了洋布,有人又把它称为土布。洋布虽然好看也时髦,但村里的老人们仍固执地认为,山花布就是比洋布好,洋布做的衣服穿在身上虽然漂亮,却不如山花布做的衣服舒适暖和。当然,说这话一般指的是做棉衣和棉被。所以,至今山里人套棉被仍坚持用棉布,而不用其他化纤类布料。
姥爷织布大约织到1958年,已经七十多岁的姥爷作为村里的五保户被送进了公社敬老院。姥爷和姥娘一共生了三个孩子,娘上面有个哥哥,下面有一个妹妹。我舅去世得早,在我的记忆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舅舅。我舅和妗子生了三个女儿,舅舅走后,妗子一直守着三个女儿过。妗子是一个坚强的女人,我三个表姐,在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、山村人对女孩上学还不认可的情况下,她就毅然把两个表姐同时送到滕县第九中学读书,并一直供她们读完初中。我姨走得更早,听娘说她在出嫁到城头乡卞庄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,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留下。
敬老院设在我们村东面的尚岩村,两村相距不到四里地。姥爷住进敬老院时,我还不到十岁,娘当时还在世,不过她已病了多年,身体一直不很好。期间给姥爷送衣物,娘都是差我去。当时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,我每次去给姥爷送东西,他都会把平时省下来的一包袱窝头让我带回家去。两年后姥爷得了一种老年病,生活不能自理,他的侄子才把他接回村里,不久就去世了。姥爷中年丧子丧女,我姥娘也先他而去,对他来说人生是很不幸的。姥爷在世时非常感念党和政府对他的照顾,让他的晚年衣食无忧。姥爷活到八九十多岁,在当时来说已算得上是高寿了。
自从姥爷住进敬老院,因为没有人继承他的手艺,加之当时形势也变了,织布机就被闲置起来。后来妗子嫌织布机搁在屋里占地方,就找人挪走了。再后来我去唐岭给姥爷姥娘烧纸时,就再没见过那台织布机。
我娘是在我姥爷走后不到两年离世的,当时给我和弟弟缝的孝衣和给亲戚们破的孝还是姥爷当年织的布。我爹说我娘就是个穷命,半辈子死会过,一床棉被盖了多年,硬是不舍得换个被里被面。其实我对娘还是理解的,她一直留着姥爷织的布不舍得用,她是在给自己留一个念想呢。
人生太短,岁月太长。转眼姥爷已经走了有六十多年了,每每想起他,我脑海里还总会浮现出那台织布机,耳畔瞬间会响起咔嗒咔嗒的梭子声。说来也巧,那次妻子写《种棉记》,我和妻子扯起乡村种棉往事时,无意中说到我姥爷会织布,家里原来有一台织布机。她笑了,说:这么巧,我爹也会织布,我家里当年也有一台织布机,不过后来被破坏了。妻子的话让我又想起姥爷的织布机,心想姥爷即使能活到今天,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,他那台织布机也早该成了老古董,也一定会被送进民俗博物馆了。我们正处于新旧两种文明的碰撞中,这也是文明不断得以进步的基础。旧的物质文明被新的物质文明所淘汰,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,单纯地维护或单纯地抛弃,都会对社会文明造成严重的破坏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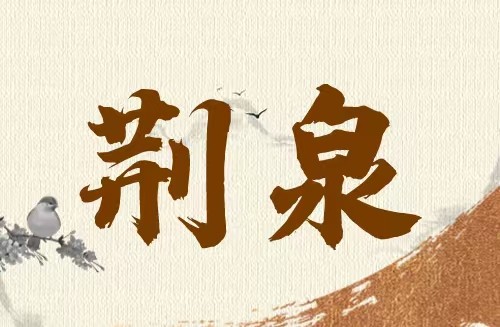

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