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燕开良
清风徐徐,艳阳高照,我驾车前往故乡燕庄。车飞快地奔驰在北留路上,隔着车窗玻璃,我看到了路两边的麦田,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着,犹如在大地上抖动一床硕大的黄色绒毯。我心情舒畅,不由得放下了车窗玻璃,瞬间飘进来阵阵小麦的清香。麦子熟了的情景,勾起了我对生产队时期收麦子的回忆,殷殷之情洋溢于笔尖。
五十多年前,农村还处在人民公社时期,土地属于生产队集体耕种、集体收获,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,生产队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,按劳分配,生产队长就是生产队里的当家人。记得,每年麦子抽穗、灌浆的时候,生产队就安排护坡人员保卫麦子。看坡的人晚上到麦田边巡逻,白天做一些稻草人插在麦田里,驱赶偷吃麦穗的麻雀。星期天,我们在河畔、坑边、地头割草或放羊,累了饿了时,就趁着护坡人不注意钻进麦地,掐几穗绿头麦穗,坐地上搓去麦芒,吃点麦仁打打牙祭,有时也掐两把到河堤下用火烧去麦芒,再烤一会,搓去麦壳充饥。
麦子成熟的时候是一大景观,田野里一片金黄,麦浪翻滚,麦穗飘香,只是那时候饿着肚子无心赏景,身在景中不识景,但看着颗粒饱满的麦穗心里很踏实,有点望梅止渴的感觉。收麦子是农村一年中第一场大战役,一般提前一个月做准备。生产队要先碾轧一大块晒麦、脱粒、扬场的打麦场。其场地,有的年份是空闲地,有的年份是生产队初春种植的菜地。若是菜地,就需要先收割青菜分给各家各户,然后整平,洒上水,铺上麦穰或麦糠,几个劳力拉着碌碡碾轧几遍(若忙时,抽不出劳力来,就用牛拉着碌碡碾轧,但因牛踩踏地面,一般不用牛),才成为地面质硬平滑的打麦场。场里有几间屋,叫场屋,备有足够的杈子、扫帚、木锨、车辆、麻袋、绳子等农具。各家各户准备好镰刀、草帽(席夹子)、茶具,再做些好吃的。一旦麦子熟好“开镰”,就要昼夜不停地抢收,也叫“虎口夺粮(赶上天下雨,就雨天抢收)”。小麦开割前,生产队长对队里所有劳动力进行合理分工,有力气的主要劳力去收割、装运。一般情况下,三个割麦的人为一组,中间那个人在前面割(拱垄),并打腰子(打结),后面的两人把割的麦子放到腰子上,捆成麦个子,不需要专人捆麦子。打麦场里也安排部分人员,基本上是体质弱的妇女劳力,负责护理场间,把场边的防火大缸都灌满水,闲时帮着运麦的卸车,并把拉到麦场的麦子晾晒好,随时轧(辗)麦脱粒。队长还要安排两人负责烧水、送饭。收麦时学校放两个星期的麦假,让小学生也参加收麦战役,那可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,一片繁忙景象。
随着队长“开镰”的一声令下,男女劳力每人“一耩子”(一畦三耩子或四耩子;若是地面不平整,有一畦两耩子的,好浇水)三垄小麦,像攻坚战的战场一样,在地头一字型拉开了收割小麦的序幕。这时,天空越来越亮,太阳将出未出,阳光还没有照射在大地上,割麦的人们弯着腰,挥舞着镰刀,默默地你追我赶,争先恐后,谁也不甘落后,布谷鸟在空中飞来飞去,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清晰的啼唱声不绝于耳。前面“拱垄”的人,割到地头后,也不休息,就帮着后面的人割(迎头)。后面的人一边割一边捆,捆成每捆重约三十斤的麦个子。再后面就有三个壮劳力(一人驾辕子,两人拉偏套)拉着地排车,把捆好的麦个子用木(桑木)杈子挑到车上,车轮飞转,把一车一车的麦个子送到打麦场上。
割麦真的像上战场,“将士”们个个精神抖擞,斗志昂扬,紧张而有序,只听到齐刷刷的割麦声,一耩子三垄还没割到头,汗水就已湿透了衣衫。我们小学生在运出麦个子的地里拾落在地上的麦穗,有时候,清晨趁着太阳没出来,露水打得麦穗潮湿,不掉麦粒,就拉竹筢搂麦,这样收拾的效率高。等大人割麦累了,休息喝水时,我们小孩才能拿起大人的镰刀学着割几把,一般情况下,大人不允许我们割,怕我们不小心砍着腿脚耽误事。割麦子既需要技术,也需要体力,技术好、体力棒的社员,割得既快又干净,放地上也不乱,割出的麦茬也矮。割麦时,弯着腰,左手抓一把麦秆,右手挥舞着镰刀,摸根迅速割下,连续几个小时才能休息一会,体力差的人,是难以支撑下来的。记忆中,我母亲是干农活的高手,割麦子从来都是领头的,竟能把许多男劳力撇下很远。
生产队割麦子,自凌晨下地,一干就是一整天,上午和下午各休息约20分钟,喝点水缓缓劲,还要趁休息这会时间磨磨镰。午饭,生产队管菜、管汤,一般都是做上一大锅粉条大白菜,或土豆炖粉条,偶尔有点肉,有时粉条白菜炖豆腐,烧白面汤,队长派专人挑着送到田间地头、打麦场等收麦现场。饭是各家自带的食物:煎饼、菜饼子、窝窝头……大家相互谦让一番,有的干脆凑到一块吃,看上去,都吃得非常香甜。谁家的孩子,就跟着谁家的大人一块吃饭。饭后休息一会,继续割麦、运麦、晾麦……田野里除了金黄的麦子,就是低头弯腰割麦的人群,乡间的路上车水马龙,运麦的车把式们不时地吼上几声,活跃气氛,鼓舞干劲……收麦子大军一直忙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回家。人们劳累了一天,一定会浑身酸疼,但看上去,乡亲们仍带着掩饰不住的丰收喜悦。
那个年代,由于口粮缺乏,农闲时的庄户人家是不吃晚饭的,但收麦的时节必须吃,不然没有力气起早贪黑的加班干活。青年突击队、民兵连的“将士”,他们吃过晚饭后,立即集合加班往打麦场运麦个子,披星戴月,歌声、劳动号子声响彻夜空。月光下,我们这些孩子们(一般情况下,夜里不安排学生活)在打麦场里尽情地玩耍,杈子、扫帚、扬场锨都成了玩具。有的拿扫帚捂蜻蜓;有的蹲在木锨上,另一个小孩拉着跑;有的模仿电影中的武打动作:打拳、翻跟头、打滚;也有的躺在麦垛上谈天论地,海阔天空的想象,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……
麦收时节的打麦场,一天到晚都是车进车出,人来人往,显得忙忙碌碌,也非常热闹。一般凌晨五点,场间的人就起床摊场,把麦个子相互依着撑起,便于透风、透光干得快,务必在太阳出来前完成摊场任务。中午,太阳光直射,烈日炎炎,正是晾晒麦子的大好时机,场间人头戴席夹子,大约每隔两个钟头就翻场一次,将摊场撑起的麦个子再次翻腾一遍,重新撑起,让麦个子均匀地接受阳光,晾透、晒干,到了仿佛要自燃的程度时,生产队长就安排人,赶紧套牛拉碌碡碾场脱粒。碾场人牵着老黄牛拽着碌碡,在摊平的麦秆上绕了一圈又一圈,不停地碾轧,场中心的麦子容易被转到,碾压脱粒快,周边的麦秆要多转上几圈。干燥的麦秆,被碌碡碾得“噼里啪啦”作响。碾场期间,还要有人把碾过的麦秆翻过来,以防背面碾压不到。碾场要将麦秆、麦穗与麦粒完全分离,做到颗粒归仓,这就考验着碾场人的体力、毅力和耐力。烈日炙烤下,碾场人一天下来,虽头戴席夹子或草帽,但个个都晒得皮肤黝黑。
碾完场后,要起场,用杈子将碾过的已经松软的麦秆(麦穰)挑到一边,将留在地面的夹杂麦壳的麦粒用推板推掀集中,用竹扫帚清扫成堆,等起风的时候扬场。扬场人用木锨将夹杂麦壳的麦粒迎风扬起,麦粒较重会垂直落下,麦壳较轻而随风飘落到下风处,借用风力将麦粒与杂物分离,有人弯着腰用扫帚一遍一遍地扫去落在麦堆上的麦壳、麦叶等杂物。木锨铲起和扬出时发出带有节奏的声响回荡在打麦场上空,驱走了人们的倦意。没风的时候,有可能要等到深夜,甚至等到第二天天亮才起风,才可扬场。麦穰垛,一座一座像小山,林立在打麦场的周边。麦穰可作为饲料喂牲畜,也可以和泥增加泥土的韧性,更可作为燃料引火做饭。
老天总是眷顾庄稼人的,连续给十多天的好天气(艳阳天),麦子就收获入仓,人们都晒得黑黝黝的,男人们上身几乎都脱了一层皮,妇女们手上都磨出了老茧,有的起了血泡。有付出,就有收获,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:生产队留够交国家公粮的麦子,同时留足麦种和集体储备粮,剩下的小麦全部分给各家各户。记忆中,起初生产队用粗长的木杆秤称麦子分配,后期用磅秤称。社员们领到了小麦,都喜上眉梢,笑得合不拢嘴,有的一口袋(麻袋)一口袋地往家扛,有的用地排车或独轮车往家运。运回家的麦子,反复晾晒后装满了大缸小盆,收获的喜悦,寄托着代代农人的希望。记得当时农村说媳妇相媒,女方家除了看男方家的房屋外,还要看粮囤里是否有余粮,主要看小麦有多少,麦子是农民的家藏“黄金”,是细粮,麦子多,女儿嫁过来不挨饿。
如今,社会发展了,时代进步了,农村割麦用大型联合收割机,直接出麦粒,麦秸秆粉碎还田,让土地更加肥沃。生产队时期那原始落后且低效的劳作方式已成为历史,猫着腰挥镰割麦、牛拉碌碡脱粒的故事,只能冷漠地出现在子孙后代的书本里,永远像魂灵一样孤寂地游荡在田野上。镰刀、碌碡、打麦场失去了原有的功能,退出了历史舞台,定格成了满满的乡村年代记忆和浓浓的乡间原始符号。但那收麦子的热闹场景一直在我心里,每到一年一度收麦子的时节,那快乐的场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,挥之不去,成了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回忆!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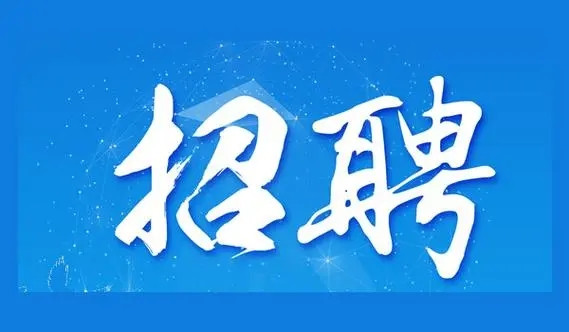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