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王新凤
午后的阳光缓缓流过窗棂,在茶杯里投下细碎的金斑。小区后花园里,菊花盛开,桂花飘香。那香气一阵阵飘来,不浓不淡,恰好能撩动人的情思。我坐在七楼的窗前,手捧一卷《沁园春·雪》,任目光在墨香氤氲的字里行间游走。心,便在这静谧的温暖里,渐渐飘远,飘向那些与诗魂相遇的远方。
翻开书页,淡淡的纸墨香扑面而来。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文字,此刻都苏醒了,牵着我走进一座无边的殿堂。耳畔仿佛飘来笙箫的悠扬、牧笛的清越,还有若隐若现的叹息——是离愁,是别绪,是说不尽的人生况味。我心里的万千思绪,渐渐汇成一脉清泉,静静地流入这诗的国度。诗人们啊,恰似园中竞放的百花,各有各的姿态,各有各的芬芳:李白的恣意,是牡丹的雍容华贵;李清照的清愁,是秋菊的冷艳傲霜;曹操的苍茫,是松柏的遒劲参天;而毛泽东的磅礴,便是那映日荷花的别样壮阔。
品味李白,便是触摸盛唐最滚烫的脉搏。他的诗,是缀在唐诗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。那浪漫到极致的想象,仿佛天地万物皆可入酒,醉成不朽的诗篇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——这是何等的疏狂与洒脱;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——这又是何等的自信与豁达。余光中先生说得最是贴切: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,就半个盛唐。”读他的诗,胸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,让人也想跟着他扶摇直上,去摘那天边的星月。
品味李清照,则是在一阕阕词里,走完一个女子跌宕的一生。她的一生,是被诗词浸透的一生。轻轻念出“红藕香残玉簟秋,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”,唇齿间便满是清秋的凉意与离别的怅惘。那愁,经她的笔一点,竟美得让人心碎。然而她不止于婉约,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的呐喊,气贯长虹,让多少须眉为之汗颜。也难忘她那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少女情态,一个回眸,便将青春的娇憨与好奇,永远定格在宋词的画卷里。她的愁,是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无奈,是“梧桐更兼细雨”的缠绵,到了最后,终是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”的千钧重量。
品味曹操,遇见的是乱世中沉郁顿挫的雄浑。这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枭雄,在历史的烟尘外,亦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诗人。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,他写下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;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的壮阔胸怀;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,他发出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的深沉悲悯。而最震撼人心的,莫过于那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慷慨高歌。即便双鬓染霜,那建功立业的火种,从未在他胸中熄灭。
目光回到当代,品味毛泽东,便如同展开一幅与中国革命同呼吸、共脉搏的壮丽长卷。他是一位将星火与诗意熔于一炉的诗人。他的笔下,既有“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的青春之问,也有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的革命乐观;既有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坚定无畏,也有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”的历史慨叹。于他而言,昆仑之巅是笔,华夏大地是纸,黄河长江是那永不枯竭的墨。炮火与莺啼,皆可入诗;长缨与百舸,俱成意境。他诗中的每一个字,都仿佛与一次战役、一段征程、一种理想血肉相连,共同铸就了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。
诚然,诗人只是毛泽东众多身份之一。他有更宏大的棋局要布,更艰巨的使命要担。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,他是运筹帷幄的统帅;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里,他是宣告新纪元到来的巨人;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,他是带领人民重整山河的领路人。他的诗情,从未脱离这片土地上的烽火与耕耘、探索与辉煌。历史给了他磅礴的激情,他也将个人的才情,毫无保留地挥洒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合上书卷,那些被文字浸润过的灵魂,仿佛已在文学的殿堂里化为永恒。他们的轩昂意气,久久地将我感染。蓦然回首,窗外的鲜花仍在不知疲倦地绽放,百般妖娆。那弥漫在整个小区的芬芳,丝丝缕缕,沁人心脾——这萦绕不散的,究竟是花香,还是那千年不散的书香呢?我已沉醉其间,无从分辨了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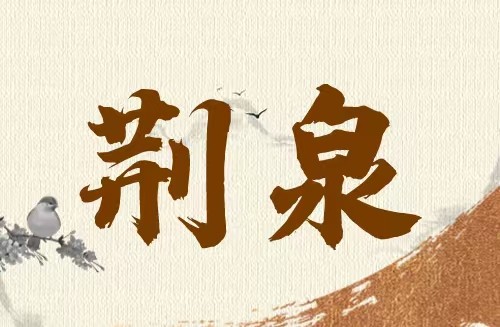

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