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侯贺奎
清晨,当时针指向6:25分,滕县广播站播放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通过红色电波在善国大地响起。这时,从县城到农村,从东山到西湖,在千家万户的广播喇叭里,正同频播放这激昂的曲子。一曲终了,接下来播放提前录制好的开头语,预告全天节目内容。播音员声音洪亮脆爽,甜圆温润,让听众如沐春阳,如临惠风。从广播喇叭里发出的开头曲又恰似军营里的起床号,它跨越时空,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。在县城工作的工人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前行,农民扛着农具开始下地干活,孩子们背起书包急忙向校园走去……
在20世纪中期,广播喇叭成了主流媒体,成了党与群众心心相连、交流信息的纽带和桥梁。滕县广播站建于1956年7月,至1985年,全县广播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县至22个乡镇广播线路达到1487杆公里,4563线公里,广播喇叭突破27万余只,农村通播率100%,喇叭入户率97%。
我很荣幸,在70年代成为滕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。高中毕业后,一边教书,一边参加农事劳动。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,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,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新人新事。入夜,微弱的灯光下,我把这些记录下来,赶写一篇篇新闻稿件。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广播喇叭里,成就感、荣誉感随之而来。
在这期间,我有幸结识了县广播站的几位编辑老师,像颜淑清、张宗石、马运法等,与他们亦师亦友,学到了不少新闻专业知识,有时我还带上稿件骑着自行车赶往二十里远的县广播站,亲自聆听几位老师的指导。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,我学会了如何抢抓新闻线索,如何把广播稿写得口语化,让不同层次的听众便于记忆。连续几年,我被评为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。
正是我与广播喇叭的这段缘,使我的人生实现了新的转折。1985年6月,我从一名教师,被选调到我所在的城郊乡广播站做编辑。在社改乡、队改村之前,有线广播只是单一的转播上级电台节目,而这一年在全社会大办广播的洪流中,乡镇广播站有了自办节目。
作为一名编辑,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探索如何让广播成为党和政府的传话筒,让自办节目成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帮手。每天除准时转播中央和省市电台节目外,还因地制宜,开辟了《城郊新闻》《农科园地》《青少年之友》《农家生活》《妇女之家》等专题节目。自办节目播出后,不少听众反映说:广播喇叭屋里挂,党的声音送到家。广播喇叭呱呱叫,种田知识早知道。
乡镇广播站开设自办节目,在纯农业时代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农事生产息息相连。上级关于农村农业的重要通知精神,要听广播;本乡镇发生了什么新鲜事,要听广播;小麦、玉米什么时候下种,什么时候施肥,要听广播;明后天天气如何,要听广播。如果谁家的广播坏了,农民们就像丢了魂似的,像少了主心骨一样。每天从广播里发出的声音,成了农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城郊乡广播站自办节目,在滕州市广播电视局的指导下,编播质量不断提高。1985年6月1日,韩桥管区5000亩小麦遭受雹灾,造成绝产。广播站编播人员聚焦灾情,赶赴现场实地采访,连续一周编播灾区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新闻稿件,从而鼓舞灾区群众战胜困难,夏粮损失秋季补,誓夺全年大丰收。1990年10月、1993年11月,由城郊乡广播站选送的《秋种专题》和《农家园地》节目,在全省乡镇优秀广播节目评选中均获优秀节目奖。
乡镇广播站自办节目的播出,离不开完好的机器设备。1966年城郊公社广播放大站成立,最先安装500W扩音机一台,主干线路7条,采用木杆、14号铁丝运行;1985年,政府加大投资,增设扩音机3部,录音机3部,增音机1部,配备调频接收机,实现专线传输与调频发射相结合的新型广播网络;之后又购进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综合播控台1套,2X275W扩音机3台,总功率达到1500瓦。主干线路从机房出发穿城而过,南线至前洪村,北线至梁场村,采用通讯电缆传输,分线后改为铁丝传送。
广播喇叭也在不断更新换代。起初的单片舌簧喇叭,先后被压电陶瓷喇叭、动圈音箱喇叭所取代,有线广播用户终端电压达到36伏,确保农户的收听效果。至上世纪90年代初,调频喇叭进入千家万户。城郊乡的广播事业同全市一样,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。一个拥有89个自然村、15000农户、72000人口的城郊乡,有线广播入户率达到98%。田间地头与农村院部的高音喇叭超过千只。
进入21世纪,随着科技的发展,农村有线广播被有线电视所取代。有线广播虽已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,但在半个世纪的流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,它成为一种文化符号,在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,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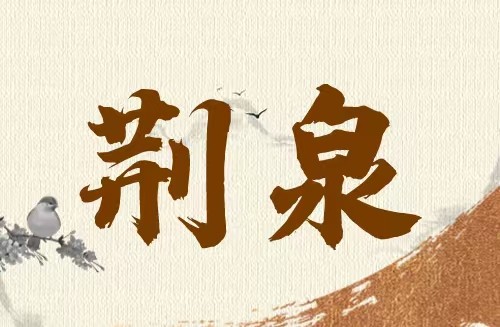

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