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侯贺奎
秋风起,“霜降”至,两场霜雪落过,大地上的红薯叶由绿变黑,由黑变成干枯。时令告诉人们,红薯该收获了……
在故乡,每年农历三月,庄稼人要忙着栽植红薯。一根根薯藤,扦插在土壤的垄墁上,半月就能长出一尺、二尺的藤条,半月之后,分枝越来越密,藤蔓越来越长,那些枝叶渐渐地遮严土地。这时的田野被绿色覆盖,于是就有了生命力。远望,像一片片翠绿的湖面,轻风一吹,碧波荡漾。
在北方,但凡禾谷类的小麦、玉米、高粱及豆菽类的农作物,它们的繁育靠一粒粒种子,只要适时播入土中,就可冲破土层,生根发芽。红薯却另类,它是靠着一根根藤蔓,年复一年的延续生命。在我们这里,红薯是主要粮食作物。在种植上要经历留种——育苗——移栽三个阶段。留种,把当年收获的地瓜,精挑细选,然后轻拿轻放,小心翼翼地存入生产队的大屋窖进行恒温贮藏,以便安全越冬;育苗,次年开春,库存的地瓜通过人工二次搬运,转移到地炕上加温育苗。火从地生,暖从脚起,其热融融,红薯遇热发芽,很快就长出挨挨排排的藤蔓;移栽,清明节过后,农历三月下旬,正是春茬地瓜最佳栽植期。生产队长统筹安排,各路人马迅速出动。一望无际的田野,尽是忙碌的身影。年长的庄稼汉手持镢头,前脚迈一步,后脚跟一步,很有规则地在垄墁上刨埯,那株距不长不短,米尺一量,正好三十公分。随后,增施农家肥,挑水浇埯,放置藤条,埋植抹平土墁。
人民公社时期,种植红薯就是最主要的农事活动。农民唯一的生活依靠就是地瓜。没有它,人就会挨饿,就难以生存。自从把藤蔓栽到地上起,庄稼人就眼巴巴地看着它成长,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根根藤蔓上。
整个夏季,地瓜生长期的管理是不敢放松的。庄稼人要把心血与汗水挥洒到黄土地里。当地瓜秧爬满坡,人们就隔三差五地下地劳作。手中的杆子不停地左右翻动,把藤蔓扎下的根高高挑起,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结大瓜。秧子翻过,再去除杂草,防止与地瓜争养分。当炎热而漫长的夏季过后,地瓜进入成熟期。垄上垄下,全是干裂的口子,从裂缝中可清晰看到下面的红薯,看到新的希望所在。
地瓜收获季,大约一个月时间。装满地瓜的地排车车队,从田间运到村里,一部分入库大屋窖。另一部分留在地里擦成瓜干原地晾晒,然后交售给国家。剩下的一点点才分配给农户食用,当作过冬的食粮。待地净场光,农家的孩子们挎着杈头下地捞红薯。他们手执小镢头,在凉嗖嗖的秋风中刨啊,翻啊,一遍又一遍,把落下的地瓜一个个找回来。从秋到冬,再到来年春天,田野里尽是青少年弓腰驼背的身影。他们的劳动所得,无疑是在帮助家人补给短缺的食粮。
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几个春夏秋冬里,我吃着地瓜长大,因此与红薯结下了不解之缘,终身念念不忘。艰难的岁月里,是红薯让我让乡亲们填饱肚子,维持生计。红薯,成了那一代人的救命稻草。
饮水思源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把红薯从国外引种到中国的陈振龙。有关资料记载:明万历年间,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有个名叫陈振龙的读书人,科举不第,转而经商,往来于福建和吕宋(明时即菲律宾)之间。在吕宋,陈振龙发现红薯藤随栽随活,就截取了几尺茎叶,切成小段,想把它带回福建。当时,菲律宾明文规定禁止红薯出境,陈振龙便把薯藤编到缆绳里,经过七天七夜航行,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下旬带回福建厦门。陈振龙在自家试种成功,后请求官府推广。
清朝时期,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,于康熙初年将红薯引种到浙江,他的儿子陈世元又带着晚辈赴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推广。红薯种植面积达到一亿多亩,成为仅次于稻米、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。一根薯藤拯救了中国三亿多人口。
在当代,杂交水稻之父,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袁隆平,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把毕生精力用在了杂交水稻的科研攻关上,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,养活了半个中国的人口。他还向亚州、非州一些国家推广杂交水稻三千万亩,靠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;农民发明家李登海,被称为杂交玉米之父,30多年间,先后选育玉米高产新品种80多个,7次开创和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记录。
当人们衣食无忧的时候,怎能不感恩党,感恩那些为粮食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们?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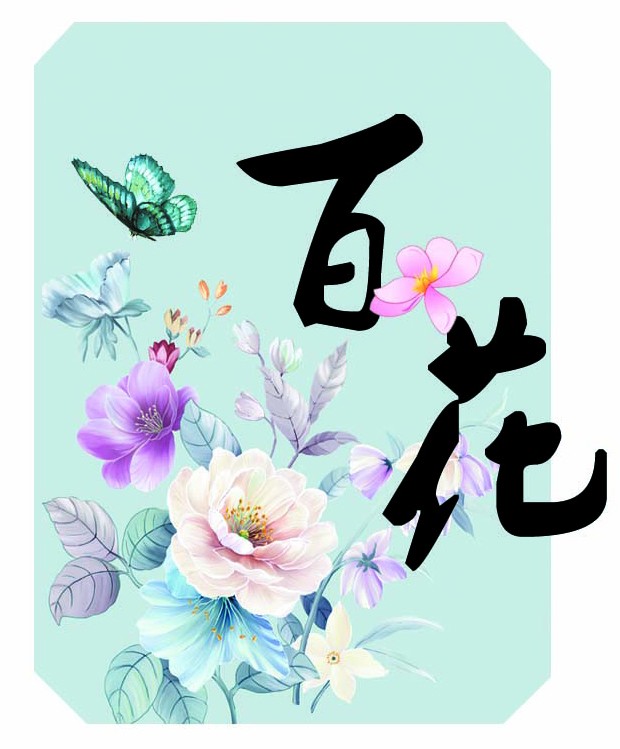


 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鲁公网安备 37048102001001号
